
| 服务热线: 13384778080 |
 |

| 服务热线: 13384778080 |
 |
来源:河北日报 |
关键词:作家 刘醒龙 对话 |
发布时间:2019.01.13 |

刘醒龙,1956年生于湖北黄州,著名作家。现任湖北省文联主席,《芳草》文学杂志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凤凰琴》《秋风醉了》《分享艰难》,长篇小说《威风凛凛》《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痛失》《弥天》《圣天门口》《天行者》《蟠虺》《黄冈秘卷》,长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上上长江》等,曾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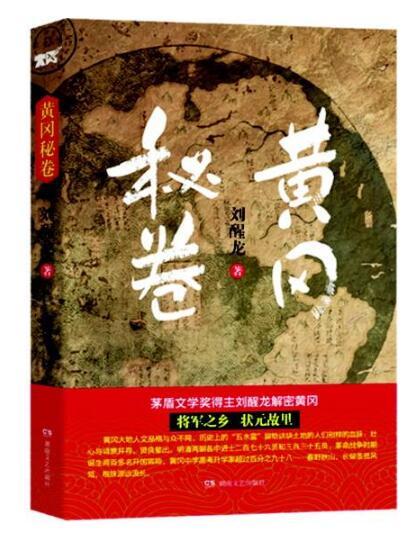
利落的寸头,匀称的身材,时尚的黑框眼镜,简单合体的休闲服……近日,著名作家刘醒龙做客河北文学馆读书荟活动,带来一场题为《文学的正途》的讲座,分享多年来他在文学创作实践中收获的心得与经验。记者眼前的刘醒龙精神干练、思维活跃,很难想象他已过耳顺之年。从1984年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黑蝴蝶,黑蝴蝶》至今,35年来,他锲而不舍地躬耕于文学田园,结出一个又一个硕果: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蟠虺》《上上长江》《黄冈秘卷》等作品相继推出,备受文坛关注……
“写作是过日子,获奖是过年。过年是大家找个机会热闹一下,但重要的仍然是过日子。”刘醒龙如是说。在石期间,记者对刘醒龙进行了专访,且看他如何用辛劳和汗水把这“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写作要自始至终尊崇内心的想法,这也是一种创作的‘初心’”
记者:您自2011年获得茅盾文学奖后,依然笔耕不辍,保持着强劲的创作势头,推出了多部高质量的作品。长篇小说《黄冈秘卷》是您的最新力作,并入选日前揭晓的2018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可见读者和业界对它的认同。我们注意到,在这部作品中,您用了“我们的父亲”这种特别的称谓,通过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命运变幻,表现出刘氏先人的勤谨耐劳、忍辱负重、正直忠勇、执拗端方的品质,进而追溯一种地方性文化的根脉。这种文化的根脉,是否就是您在书的后记中提到的“贤良方正”?
刘醒龙:也可以这么说。其实,当初在书写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并没有太多想法,处处随着性子,凭借着一种创作的感觉引领着自己写下去。直到写完后静下来,我才突然意识到这部作品的意义。2005年出版长篇小说《圣天门口》,我在写作过程中曾有写成史志的想法,出版后却被广泛理解为书写家族。而《黄冈秘卷》的情况正好相反,小说刚一发表,就被定性为史志,而我本来只是想好好写一写几位很有代表性的父辈。在后记中,我写了一句话:“为故乡立风范,为岁月留品格。”我一直觉得,养育我们的故乡是非常伟大的,只是我们并没有深入了解过它,对它的品性常常视而不见。
年轻时我对故乡有种种偏见,现在越走越发现,故乡太了不起了。有一种品质,潜藏在祖祖辈辈的先人血脉中,和他们一起生长。从爷爷到父亲,再到故乡千千万万的乡亲,他们都是普通人。四十岁以前,我看重他们身上的血性,如今,我更看重从他们身上延续到自己心里的血脉,常常被他们身上那种贤良方正的细小印记所震撼。这种被细小印记所带来的感动,恰是与内心彻底融合的沧桑。
记者:看来,您的父辈以及故乡对您的生活和创作有着很大影响。
刘醒龙:是的,父亲对我们而言,不是纪念碑,而是有血有肉的、鲜活的、有影响力的一个人。2012年深秋,父亲在88岁上病逝,这个年纪也算是高寿了,但我心里还是没有丁点准备。这个准备不是说后事什么的,而是自写小说以来,一直觉得父亲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很精彩的小说,至于是不是真的写写父亲,我并没有认真想过。在给父亲守灵到最后送别的几十个小时里,我流着泪写了一篇散文《抱着父亲回故乡》,那样的文字是后辈对长辈的纪念与情怀,真的用它来言说父亲这辈子,是远远不够的。父亲他们这一代人的理想和情怀,放在时间的长河里来看,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越是用心去写,越是发现他们这一代人看上去平凡普通,貌不惊人,但在他们所面对的岁月里,其心其意,其行其为,远比通常所见的那些肤浅文字来得深刻和高尚。而用“我们的父亲”这样的称谓,也是为了表达作为后来者的“我们”,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90年代的“写实”,在又一个百年的背景下,为“父亲”铸造一尊令我们问心无愧的文学雕塑,这理应成为与“父亲”最亲近的“我们”的责任。
记者:您的这种创作状态真的很令人羡慕。对于一部长篇小说,在写作前不去预设而能够无拘无束地随性创作,对很多作家来说可能是难以想象的。您是如何达到这种境界的?有没有什么可以传授的写作技巧?
刘醒龙:写作要自始至终都尊崇内心的想法,这也是一种创作的“初心”。自己渴望写什么,笔端就自然而然地流淌出什么,不能硬写。我写《黄冈秘卷》这部作品时,有一种自由洒脱的境界,如果非要找一个原因的话,可能就是通常所说的无欲无求。
有些作品在阅读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作家在写作时是有一种欲望在推动着前进的。比如《基督山伯爵》字里行间都弥漫着复仇的情绪。写作要投入,但我不提倡过度投入。投入过度往往容易使自己陷进去,造成作品中欲望太过张扬。写作时,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情绪高涨时要让它平息一些,情绪低落时就需要停下来等一等。豪情万丈状态下写出来的漂亮文字,回过头来看是不真实的、靠不住的。
写小说一定要有故事,在小说中设置“包袱”,对小说中的所有人物负责到底,对笔下的人物进行系统管理,哪怕这个人物在开篇只有二三十字的描写,也要在后面有所交代,这是一个作家的责任心。这些都是写作的基本技巧。基本技巧永远不会过时,是符合写作的基本规律的,关键看作家如何利用、体悟和表现。
记者:谈到写作技巧,您的几部长篇小说,不管是六年三易其稿的史诗性长篇小说《圣天门口》,还是《天行者》《蟠虺》《黄冈秘卷》等,都立足于故乡,将宏大的时代风潮、历史烽烟与民间底层人物的命运紧紧融合,真实呈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人性嬗变的历史进程,一直在悲凉与柔情的文字中深刻反思人性。在写作中,您如何处理这种“小人物的大命运、小地方的大历史、小故事的大道理”?
刘醒龙:我们身处小地方,每天接触到的也都是小人物、小故事,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都附载着时代的变化。我生长于鄂东大别山区,那个地方的历史和整个中国的近代史其实是相通的,生长在那里的人们有着与时代同样伟大的命运,他们的生命与时代的步伐融合在一起。有人认为《黄冈秘卷》是对地方性知识的全面呈现,是一部宏大的黄冈志。其实,相比别的作品,这部小说方志特征只是手段。小说写到长辈们常常提起的“贤良方正”品质,这四个字最能概括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显然不再是一个小地方的地方志了。
文化有地域性,文化又是无地界的。福克纳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我的一生都在写一个邮票大的地方。”他为什么把自己的故乡比作邮票而不是其他的事物,比如汤匙、酒盅或者火柴盒呢?因为邮票可以通达世界,尽管它很小,却能到达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作家要进入生活深处,发现被一般人所忽略的生活真相”
记者:您曾说过,一个小人物,尤其是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小人物,一类人、尤其是一类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的精神状态与生存状态,从来就是一条贯穿自己小说的命定线索。在您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您似乎更愿意以温情的善意来谅解人性的弱点。这种“对人的关怀、对生命的关怀”是您一直以来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吗?
刘醒龙:要相信别人、相信自己都是向善的。要相信时代、相信历史、相信生活、相信自然、相信世间万物。只有相信,自己面对生活时才会更有信心。有信心,做事的动力才会强大,过程再曲折、再艰难都能够做到底。做到底就有可能成功,凡是半途而废的永远不会成功。这是一种自我修炼。我愿意寻找各种理由相信别人都是出于善意,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能想到别人的好,肯定是件快乐的事情。长此以往,会让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强大。
真正的作家、艺术家,力量来源就在于心灵的宽阔,有能力爱自己,更有能力、有胸怀去爱他人,能够在情感上深刻地贴近和进入那些看似与他无关的广大人群。
记者:您目前担任着《芳草》杂志主编,日常除了创作一定还会接触到许多作者的来稿来电。结合自身的创作经验以及编辑文学杂志的经历,您认为当下小说创作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刘醒龙:我有这样一种感觉,现在的小说变得越来越不食人间烟火了。曾经文坛流行一种观点叫“消灭细节”。这种说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缺乏对人世间的普通人日常行为的丰富想象。有些人认为,我自己也是生活中的一份子、时代的一份子,我写自己就是深入生活,就是写这个时代。这么理解当然也无可厚非,关键还要看这类作品是否与大众有情感的共鸣点。不能仅仅看到生活的表象,要看是否进入生活深处,发现被一般人所忽略的生活真相。写作的初衷是个人的,起初是从作家的眼界、胸怀出发的,但最后经过创作所呈现出来的作品,是超越个人的,应该展现带有时代共性的眼界和胸怀。
记者:近年来,您一直没有停止行走的步伐,探访南海诸岛、深入可可西里、万里长江行……这样的行走和行走中的创作,给您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感悟?
刘醒龙:2017年7月,我从长江的入海口行走至长江源头,每天遇到什么就写什么,走了40天,写了30多章,当天记下所见所闻,第二天就在报纸专栏发表。这种完全不同的文学创作经历,给了我这样一个体会:在屈原、李白、杜甫和苏东坡的时代,将万里长江从头走到尾,比21世纪的人类在宇宙边缘行走还要难。但在今天,只要我们有意愿,有激情,身体健康也有保证,普普通通的人都能做到。在不断深入生活中,我们既能发现自己作为生命个体的崇高,更能感受到国家的伟大进步。
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面对日新月异、不断变化的新时代,依然坐在书斋、不出斗室、不问世事,一心只为能写出一本可以当枕头睡觉的书,这是万万不行的。文学创作不能急,也不能不急。这种“不能急”和“不能不急”是相对的。身处伟大时代的中国作家不仅需要有直面现实的决心和勇气,更要有讲好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中国故事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前人的既有成就和当前正在创新的理念都表明,只要我们愿意为这个时代付出自己的才华,苦练脚力、脑力、眼力、笔力,自觉地用心用情用功去做,就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就能够处理好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写出更多与新时代发展同频共振的优秀作品。
记者: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您怎样看待阅读与写作的关系,平时您喜欢阅读哪类著作?
刘醒龙:最近我偏好读地方志和古文。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研究是从地方志和家谱开始的,哪怕是最普通的家谱,也能上溯十几代人。抛开这种血脉传承,只是就事论事的价值判断是没有意义的。文学艺术之所以在历史进程中从不缺席,就在于文艺作品是文化血脉的重要传承方式。
作家最应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厚养分。20世纪80年代后的写作急切需要补上向古人学习这一课。现在的文学太过于注重向西方学习,忽视了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致敬。作家应该是学贯中西的,不应该全盘西化。目前在学校的教学中,也常常割裂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没能做到融会贯通。中国作家应该多读些中国典籍,用血浓于水的传统根脉来滋养并进行当代文学实践。从长期来看,这种影响将是事半功倍的。文学创作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得靠自己一步步地小跑到位,指望别人用马来拉,也还是松松垮垮不成模样。
“关注时代是文学的根本”
记者:您在这次讲座中屡次提到,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把握中国文学传统的正脉,只有通过塑造出贤良方正的中国形象,才能为世界文明发展注入更多激情与活力。在文艺创作中,这种精神或者说文化的正脉具体体现在哪里?
刘醒龙: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不仅需要自觉沉淀的博大胸怀,更需要饱含深意的沉着淡定与执著坚守。2018年8月,我去鄂西秭归县的乐平里,拜访当地的骚坛诗社。骚坛诗社藏在大山深处屈原的出生地乐平里,有600年历史,像是历史特意珍藏的一条文学正脉,生生不息。骚坛诗社成员全部是当地的农民,他们一代接一代写了上万首诗词,农闲时候聚在一起,用古老的音韵在屈原庙前相互唱和。这些并不认为自己是诗人的农民,用写在房前屋后的诗词以及田间地头的吟唱,表达了普通人的努力和坚持,造就了潜藏在人民中间的中国文学创作精神。他们的平静与坚守告诉我们,五千年文化正脉正是在不急不缓中默默延续至今的。
又比如,热干面是令武汉人津津乐道的小吃,许多武汉人都会说自己是吃热干面长大的。实际上,除了早晨,很少有武汉人会将热干面当成正餐。如果一天到晚只吃热干面,排斥大米饭、肉类、青菜等正餐,当年的辛亥革命首义,就不大可能发生在武昌。因为可以想象,如果武汉三镇的人只吃热干面,肯定会是营养不良,满城的人都病恹恹的,哪里还有推翻封建王朝的铁血性格。这正如那种脱离了文化品格的作品,个性再突出,风格再独特,也只能成为小品,很难表现出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与发展。花絮类的东西,可以编成“顺口溜”“急就章”,见效比较快,但很难成为生活的“正餐”,人们如果只“吃”这些东西,就会营养不良。现代社会有太多层出不穷的“小吃”,这些所谓美味常常让人忽略“正餐”的重要性。无法想象,如果中国古典文学只有小吃一样的《聊斋》,只有美味的明清笔记小说,而没有提供主要文学营养的《红楼梦》《三国演义》,会是什么样子。
记者:是的,您在创作中也一直延续着这种文化的正脉。上世纪90年代中期,您的中篇小说《分享艰难》与河北文坛“三驾马车”谈歌、何申、关仁山所创作的《大厂》《年前年后》《九月还乡》等小说,一起受到评论界关注,引发了一场“现实主义冲击波”。这些作品时代感强烈,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现实主义创作潮流,在当代文坛产生了极为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如今我们身处前所未有的时代,现实生活为作家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丰富和新鲜的创作资源。新主题、新人物、新视角、新理念层出不穷,社会生活如汪洋大海,哪怕是一朵浪花都可以被作家酿成醇厚的文学老酒。然而,多元化现实生活的芜杂性、异质性、丰沛性、非逻辑性,也给创作带来了巨大挑战。那么,身为作家应该怎样面对并书写当下的时代?
刘醒龙:无论社会发展到哪个阶段,文学都离不开时代性,关注时代是文学的根本。这次来参观河北文学馆时,我重温了反映抗战时期晋察冀战斗生活的一系列经典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真切地体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我至今还记得小说《平原枪声》中滹沱河两岸的青纱帐以及令人振奋的战斗场面描写。当年,燕赵大地曾涌现出一批颇具分量的反映农民革命斗争和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比如《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小英雄雨来》等,这些都是具有鲜明时代性的经典作品,作家是在用文学的眼光来书写那个时代。同样,在我们所置身的这个时代,作家也必须用文学的眼光来观察、来思考,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学的声音。
记者:的确,文学家有时不仅仅是思想者,还是一位时刻警醒着的观察者、记录者。文学的眼光要看到日常生活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看到平常事物背后的不寻常。作家应该站在历史背后进行创作,有独立、深入的思考。那么,这种观察时代的文学眼光如何才能练就呢?
刘醒龙:作家应具备自我学习、自我成长的本领,要像大江大河一样源源不断注入新的活水。面对伟大的新时代,不仅仅是年轻作家需要提升,成熟作家也需要接受时代的挑战,不断充实自己。学校只能训练写作技巧,一部作品所不可缺少的文学元素是教不出来的,要靠自己不断摸索、总结。文学艺术是伟大而永恒的,文学艺术元素是日新月异的,作家和艺术家的认知能力、创造能力也需要不断成长。
其实,作家是一个清冷的职业,很多时候很难遇到知音,所以就需要有坚守精神,守住职业的底线。坚守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文字。在现实面前,作家不能只是旁观者,也不可以是那种随大流的起哄者。作家这一行业最不同寻常的本领,就是能够在哪怕千千万万个声音中区别出自己的声音,回过头再来影响那千千万万人。写作是一件很漫长的事,它和做任何事一样,不是看你一下子能跳得多高,而是看你能够走多远。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守住初心,沿着文学的正途,一直走下去。
■记者手记
初识刘醒龙
□崔立秋
1月5日,作家刘醒龙应邀做客河北文学馆,有幸与他一同喝茶聊天,畅谈文学与人生。
第一次听说刘醒龙的名字,是在1996年,我还在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这一年,刘醒龙的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获得了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同期获奖的还有铁凝的散文《女人的白夜》、迟子建的短篇小说《雾月牛栏》和何申的中篇小说《年前年后》等。当时,中国文坛上正掀起一阵“现实主义冲击波”,主力军是河北文坛的“三驾马车”何申、谈歌、关仁山,刘醒龙的名字赫然在列,而且排在了“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最前面,俨然是一位领军人物。
真正阅读刘醒龙,是从长篇小说《天行者》开始,大山深处界岭小学师生庄严的升旗仪式深深打动了我。2011年8月,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刘醒龙的《天行者》从众多候选作品中脱颖而出,同时获奖的还有莫言的《蛙》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等。9月,我去北京采访莫言和刘震云时,曾以媒体记者身份参加了在国家大剧院举办的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刘醒龙,他个子不高,短发,人长得很精神。评论家陈晓明宣读了授奖词,赞誉“《天行者》是献给中国大地上默默付出的乡村英雄的悲壮之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亲自为刘醒龙颁奖后,刘醒龙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此时此刻无望无际,生命之上诗意漫天!”
2016年5月,刘醒龙应评论家郭宝亮之邀到河北师范大学做了一场题为《文学:仁者无敌》的讲座。那些日子里,工作之余我正在焦头烂额地准备博士论文答辩,最终还是挤时间去听了这场讲座。刘醒龙以孟子的“仁者无敌”为核心,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尤其是新作《蟠虺》,讲述了一个作家对文化血脉的传承,以及民族精神的坚守。虽然他的小说多是现实题材,但是刘醒龙给我的印象却是一位有着仁爱之心的传统文化守护者。
前几天,刘醒龙参加河北文学馆读书荟期间,我和同事对他进行了面对面的专访。在谈到他对阅读和写作、故乡和文学、生活与时代等的理解时,刘醒龙说,一个作家要守护好自己的故乡和文化的血脉,要用文学的眼光审视生活,书写所置身的这个伟大时代。后来,我们去聆听了他的讲座《文学的正途》,他从“春秋大义”讲到“贤良方正”,最后呼吁作家要坚定文化自信,努力塑造时代新人。讲座开场之前,刘醒龙在老朋友省作协主席关仁山陪同下参观了河北文学馆,并即兴挥毫泼墨,写下“中国文气,燕赵雄风”八个大字,向底蕴深厚的河北文坛致敬。
1月9日,作家张楚的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他写作家阿摩司·奥兹的文章《一次相逢》,文中引用了奥兹关于写作的一句话:“对于我而言,写作并不是激情,与之相反,是一种强迫症。”刘醒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道:“作家是一个清冷的职业,很多时候很难遇到知音,所以就需要有坚守精神,守住职业的底线。”
(肖煜 张晓华)
|
Copyright © 2015 西部散文学会 Power by www.cnxbsww.com 

地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 |